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11-21 17: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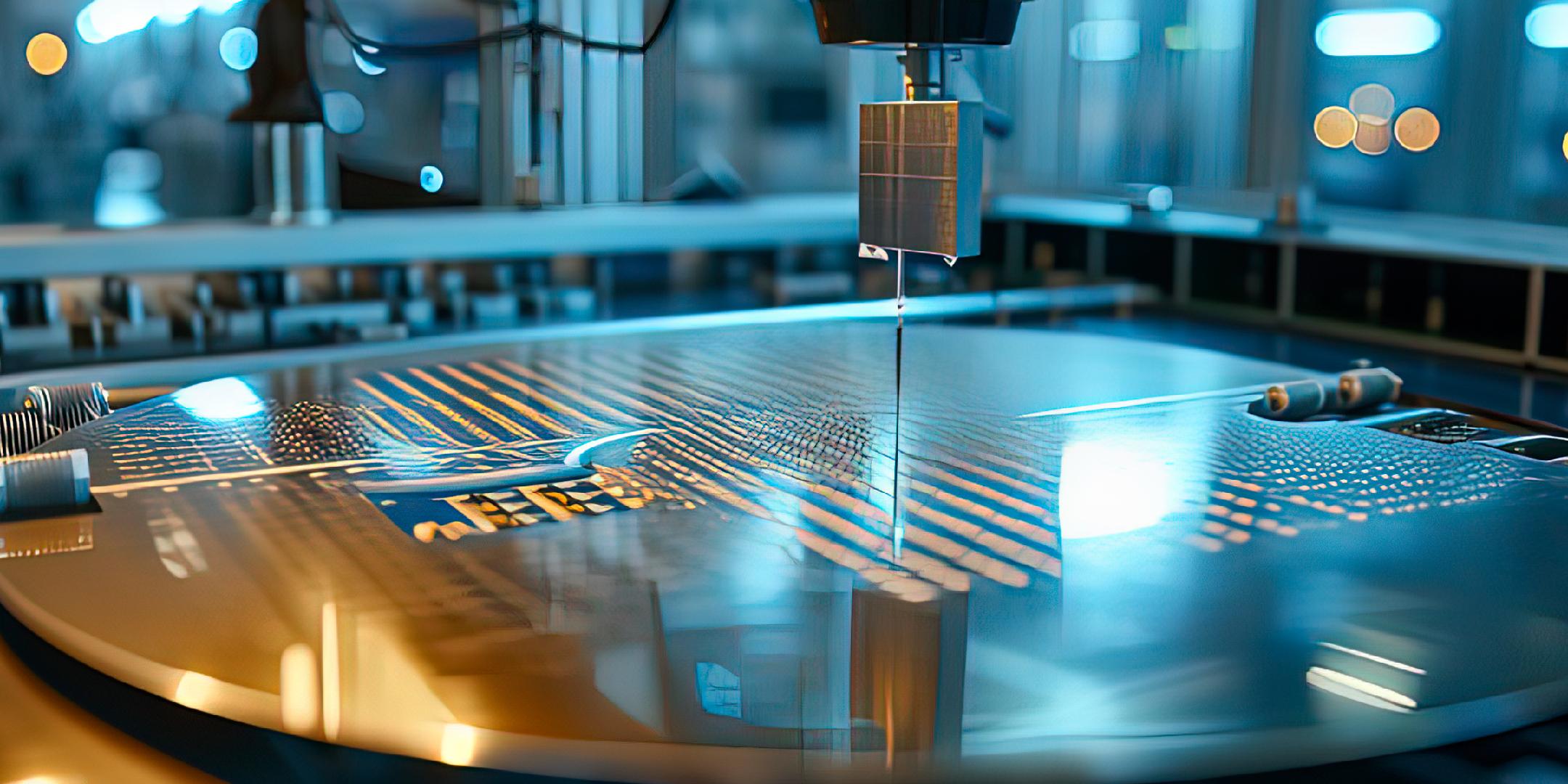
經濟觀察報記者 鄭晨燁
11月20日,在深圳華強北電子世界,主營內存產品經銷的楊先生現在的感覺很復雜——就在去年這個時候,他還在發愁怎么處理手里堆積的內存條,甚至動過關店轉行的念頭。“(去年)覺得這行沒盼頭,價格說反彈了好幾年,也沒什么起色。”楊先生說,但現在,他唯一的煩惱是不敢接單。
“去年的煩惱是沒生意,今年的煩惱是生意來了不敢做。”楊先生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現在一款主流規格的DDR4(第四代雙倍數據速率內存)內存條,價格相比年初已經翻倍,更要命的是,上游總代頻繁“封盤”,“那是真沒貨,不是捂著不賣”。
在這個并不大的柜臺里,報價單已經基本作廢了,客戶打來電話詢價,楊先生現在的標準動作是,先掛斷,給上游打個電話確認,才敢回撥過去報價。他苦笑著說,現在做生意像是在“走鋼絲”,手里沒貨不敢空轉,怕接了單子交不出貨。
非理性“瘋狂”
如果只看價格走勢圖,不看成交量,市場會以為存儲行業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繁榮。
根據知名科技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集邦咨詢于11月20日發布的最新報告,從今年9月初到現在,短短兩個多月時間,DDR5 2Gx8顆粒(第五代雙倍數據速率內存)的現貨價格環比大漲了307%。在NAND Flash(閃存,主要用于手機存儲和固態硬盤的非易失性存儲器)方面,512Gb TLC Wafer(制造大容量存儲芯片的原始晶圓)的現貨價格近期也曾一度出現單周漲幅接近15%的情況。
這種漲幅放在任何一個商品市場,都足以被稱為“瘋狂”。這種“瘋狂”在零售端也肉眼可見,11月20日,記者登錄京東、天貓等國內主流電商平臺發現,多個主流品牌的內存條價格均處于高位,以一款熱銷的16GB DDR4筆記本內存為例,其售價已從年初的200多元漲至500元左右,價格翻了一倍多。
11月18日,知名存儲市場研究機構CFM閃存市場分析師楊伊婷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用“一周一變”甚至“一天一變”來形容當下的存儲芯片現貨價格。她告訴記者,現在的市場處于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存儲原廠(擁有晶圓制造能力的存儲芯片廠商)對于現貨市場,已長期處于“未明確報價”的狀態。
這種“不報價”的沉默,在市場上被翻譯成了各種恐慌的信號。就在幾個月前,市場還在討論“DDR4價格倒掛”的怪象——當時是因為存儲原廠要停產老款DDR4,導致老款DDR4比新款DDR5還貴,但現在,這種局部的供需錯配,已經演變成了全品類的價格瘋漲。
但終端市場的回暖速度,顯然沒能跟上價格的漲幅。
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統計,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為3.227億部,同比僅增長了2.6%;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約6840萬臺,甚至出現了0.6%的同比下滑;而在PC端,即便有Windows 10服務終止帶來的換機利好,全球三季度出貨量也僅為7580萬臺,同比增幅為9.4%。
這種個位數的增長,顯然撐不起上游動輒翻倍的漲幅。
11月13日,經濟觀察報記者以投資者身份致電A股頭部存儲模組廠商佰維存儲(688525.SH),該公司董事會辦公室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這輪價格上漲主要是由上游晶圓廠決定的”。該名工作人員同時表示,對于原廠來說,目前對擴產是比較謹慎的,原廠不希望像2023年一樣大幅擴產,導致大家內卷,價格下跌,而是希望能維持當前的高景氣度。
換言之,當前存儲市場的熱度,更多源于供給側的主動調節,原廠通過控制晶圓的投放節奏,在需求端尚未全面走暖的情況下,支撐了價格的上行趨勢。
那么,原廠把產能控制住之后,原本應該生產手機和電腦內存的晶圓,到底去哪了?對此,楊伊婷告訴記者,“本輪漲價的直接導火索是北美AI服務器需求的爆發”,從三季度開始,以谷歌、微軟、亞馬遜為首的大型云服務供應商(CSP),為了建設AI數據中心,涌現出了海量的存儲需求,但這些云服務巨頭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內存條,而是高帶寬內存(HBM)和企業級固態硬盤(eSSD)。
對于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這三家掌握全球95%以上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產能的巨頭來說,HBM和eSSD是一道必選題:賣給手機廠商的LPDDR(低功耗內存,主要用于移動設備),價格透明,利潤微薄,還要陪著客戶卷參數;而賣給AI服務器的HBM,是當前算力競賽的“入場券”,不僅單價極高,而且客戶根本不還價,只求有貨。
例如,三星電子發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財報就顯示,當季公司存儲業務營收達到26.7萬億韓元(約合187.7億美元),環比增長達26%,財報特別提及,受AI服務器需求驅動,HBM的銷量環比增幅超過80%,在隨后的財報電話會議上,三星電子內存部門副總裁金在俊更是直言,預計明年主要客戶的需求將超過三星自身的供應能力。
相比之下,未能深度切入AI市場的存儲廠商則嘗到了苦果。11月14日,日本存儲巨頭鎧俠(Kioxia)公布業績,其2025財年第二季度(7月至9月)凈利潤僅為407億日元,同比下降超過60%,這份“暴雷”的成績單,甚至在當天引發了A股市場存儲概念股的大跌。
為何在全行業都在享受漲價紅利時,鎧俠的利潤卻在縮水?財報顯示,因智能手機季節性備貨,其智能設備產品營收占比激增至35%,環比大漲99%,但這類面向手機的存儲產品利潤率較低,且受制于大客戶的固定價格協議,無法像HBM那樣享受溢價。
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存儲原廠的策略會非常“理性”——將有限的晶圓產能、封裝產線和研發資源,毫無保留地切給AI。另外,楊伊婷亦向記者表示,原廠在2023年虧損嚴重,所以并沒有對2024年的晶圓產能進行大規模投資,即便現在決定增加資本開支,挖地基、蓋廠房、買設備、調試產線,這一套流程走下來,實際產能釋放也要等到2027年或2028年。
也就是說,在未來的兩三年里,全球存儲芯片的總產能池子是鎖死的,AI多吃一口,消費電子就得少吃一口。
11月18日,TrendForce集邦咨詢分析師王豫琪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也強調,目前存儲芯片漲價的主要驅動力仍是來自AI需求爆發,消費型需求目前并無太大成長。楊伊婷則告訴記者,目前原廠對AI需求的滿足率也僅有50%—60%,這意味著,連最賺錢、優先級最高的AI客戶都喂不飽,原廠根本沒有多余的精力去管那個“碎片化”的現貨市場。
在楊伊婷看來,存儲市場目前實際上已被割裂成了兩個平行世界:其一是“合約市場”,屬于字節跳動、阿里、騰訊、小米、聯想這些大客戶,它們和原廠簽有長期戰略合作協議,原廠為了維持基本盤,會保障它們的剛性需求,不會斷供,漲價幅度也相對溫和,是“逐季度穩步攀升”;其二則是“現貨市場”,屬于中小模組廠、渠道商和無數的中小品牌,它們沒有直接的產能分配權,只能在存儲原廠“吃剩”的資源里搶食。
“在原廠產能分配極其緊張的現狀下,非AI領域的供應受到擠壓。”楊伊婷說,因為拿不到原廠的直接供應,中小客戶只能被動接受高價,市場上那種“一日一價”的劇烈波動,主要就發生在這個領域。對此,中芯國際(688981.SH)聯合首席執行官趙海軍亦在三季度業績會上表示:“AI行業占用了大量存儲產能,導致碎片化、少量多樣的存儲市場被大供應商放棄。”
這種放棄,對于原廠來說是戰略聚焦,但對于依賴現貨市場的中下游企業來說,就是一場災難。因為,在過去,存儲行業的邏輯是“水大魚大”,只要消費電子的終端出貨量在漲,大家都有飯吃。但現在,邏輯變成了“存量博弈”,甚至是“減量博弈”,因為原廠已經找到了比手機和電腦更賺錢的生意,它們不再需要通過“薄利多銷”來維持工廠運轉。
這對于消費電子產業鏈上的廠商來說,現在的處境就十分尷尬:終端市場的需求還沒完全回來,上游的零部件成本卻已經先漲起來了。而且,這個局面在短期內無解。
楊伊婷告訴記者,預計明年全球服務器存儲位元需求將增長40%—50%,而供應端的產出增長僅為20%—30%,供需增速的剪刀差,注定了“缺貨”將是貫穿2026年的關鍵詞。趙海軍亦在中芯國際三季報業績交流會上指出:“當前存儲供應缺口至少在5%以上,存儲市場若出現5%的供應缺口,價格可能翻倍,若供過于求5%,價格可能腰斬。”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被AI定義的賣方市場里,傳統的供需調節機制已經失效,只要AI的熱度不退,存儲芯片的價格就很難回到過去那個“白菜價”的時代。
明年手機會更貴?
當上游原廠把產能切給AI,把價格拉高之后,壓力就像水一樣,順著供應鏈流到了手機和電腦廠商的面前。
11月18日,在小米集團(01810.HK)的第三季度財報電話會上,小米總裁盧偉冰直言,內存成本的飆升已經到了“提高手機價格無法完全抵消”的地步。他甚至直接給市場打了一劑預防針:“明年大家會看到產品零售價格方面可能有較大幅度上漲,包括小米、友商在內。”在他看來,雖然廠家會自己承擔一部分成本,但內存漲價實在太猛,剩下的部分只能通過產品漲價傳導出去。
兩天后的11月20日,全球最大的PC廠商聯想集團(00992.HK)也發出了類似的聲音。在業績發布會上,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對未來的判斷與盧偉冰類似,認為存儲相關的零部件短缺和價格上漲不會是短期的,預計整個2026年都將維持這一態勢。
作為應對,楊元慶還表示,聯想已與核心存儲零部件供應商簽訂了合約,確保2026年的供應保障。
對此,楊伊婷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提到了手機廠商應對高成本存儲芯片可能會采取的一個策略——“降容降配”。
“本來手機廠商計劃將今年的新機型內存標配升級至12GB,但現在因為存儲太貴,可能被迫維持在8GB。”楊伊婷表示,在LPDDR5X(主要用于中高端智能手機的新一代低功耗內存)等移動端內存價格劇烈上漲的情況下,終端廠商不再主動“卷”參數,而是選擇通過控制單機容量,來平滑硬件成本的波動。
這種策略在入門級手機和機頂盒等對價格極度敏感的產品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楊伊婷指出,目前eMMC(主要用于中低端電子產品的嵌入式存儲芯片)、LPDDR4X等成熟制程產品的價格漲幅普遍超過了50%,逼得廠商只能“減配保價”。
這筆賬如果不算清楚,很難理解手機廠商的焦慮。
根據TrendForce集邦咨詢發布的最新調查數據,2025年第四季度,DRAM合約價格同比上揚逾75%。而在智能手機的物料清單中,存儲器的成本占比通常在10%—15%之間,按照這個比例估算,僅今年一年,手機的整機成本就被存儲器墊高了8%到10%。而且,TrendForce集邦咨詢預計,明年整機成本將在今年的基礎上再提升約5%到7%。
簡單來說,對于利潤本來就微薄的低端機型而言,因存儲漲價多出來的成本或許就足以吃掉所有的利潤。
王豫琪告訴記者,目前存儲原廠的產能向AI傾斜的現象確實存在,消費型產品的訂單則主要以大品牌客戶優先滿足,而且即便是大品牌,滿足率也不是100%。王豫琪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小品牌客戶面臨的缺貨情況會更加嚴峻,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整機售價可能提高,而整機漲價反過來會影響消費者的采購心態,最終也會導致整機出貨量低于預期。
TrendForce集邦咨詢預測,品牌端勢必會調降低端產品的占比,甚至可能引發手機市場的新一輪洗牌。
在資源緊缺的時候,大品牌還能靠長約拿貨,小品牌可能連入場券都拿不到,“大者恒大”的趨勢將更為明確。
中芯國際聯合首席執行官趙海軍在三季度業績會上,則從芯片代工的角度,提供了另一個觀察終端博弈的視角。他發現,手機客戶現在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即便買齊了屏幕、處理器等其他零部件,如果買不到存儲芯片,手機也裝不出來;另一方面,因為存儲芯片漲價太猛,手機客戶在總成本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開始反過來逼迫其他芯片降價。
“客戶在其他IC定價上存在談判博弈。”趙海軍說。這意味著,存儲原廠吃掉的利潤,有一部分其實是擠占了模擬芯片、電源管理芯片等其他供應商的份額。
眼下,在這條被拉緊的供應鏈上,每一個環節都在試圖把壓力轉嫁出去。那么,壓力傳導的終點在哪里?
11月19日,曙光存儲副總裁張新鳳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的采訪。作為國內頭部的存儲系統廠商,曙光處于產業鏈的中游,直接承接了上游介質(SSD、硬盤等)的漲價壓力。張新鳳用了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來描述這種傳導:“作為存儲系統廠商肯定會挨板子,但最后這個板子還是落在用戶身上。”在她看來,這次上漲的部件涵蓋了內存、SSD和HDD(機械硬盤)三大件,漲幅基本上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了一倍到兩倍,系統廠商通過軟件優化能消化的成本非常有限,最終只能漲價。
曙光存儲副總裁楊志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更是直接打破了消費者對于電子產品“摩爾定律”的幻想——即“硬件性能會越來越強,價格會越來越便宜”的情況將難以重現。“原來設想都是每一年、每兩年投資成本會下降多少,現在看起來不太可能了。”楊志雷說,“首先下降就沒有可能性了,未來還會看到持續上漲。”
這番話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貴”將是電子產品的常態,無論是企業購買服務器,還是個人購買電腦手機,都要為上游的產能緊缺買單。
面對當前這輪存儲漲價,張新鳳在采訪中呼吁整個產業和市場要更加“理性”,她指出,目前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存儲介質的生產廠商都非常有限。換言之,當全球95%以上的產能掌握在三家巨頭手中時,它們對產能的調配和價格的把控,幾乎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不過,就在國際存儲巨頭忙著在AI的盛宴中切分蛋糕時,國內存儲廠商也看到了“喝湯”的機會。
正如趙海軍在中芯國際業績會上所稱,AI行業占用了大量產能,導致大供應商放棄了那些“碎片化、少量多樣”的市場,而這些被遺忘的市場,正是國內中小供應商的機遇。他同時透露,中芯國際的NOR Flash(主要用于存儲代碼的閃存芯片)、NAND Flash(主要用于大容量數據存儲的閃存芯片)等特色存儲產品目前訂單充足,正是得益于這種溢出效應。
楊伊婷亦表示,由于國際原廠產能優先滿足北美云服務提供商的需求,國產原廠和模組廠正在積極填補由此產生的市場空缺,尤其是在信創領域和服務器市場。“采用國產存儲是長期趨勢,缺貨潮加速了這一進程。”楊伊婷說,在缺貨潮之前,國內終端廠商就已經開始大規模應用國產存儲產品。
為了在巨頭壟斷的縫隙中尋找話語權,國內產業界也在嘗試建立自己的標準。
11月19日,中科曙光正式接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數據存儲專業委員會當值會長單位,并宣布成立Future Storage工作組,曙光存儲總裁何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此舉旨在構建存儲技術標準,打破以往各家企業用“非標性能”控標的局面,減少企業的重復投入。“以往各個廠家存儲產品在推廣過程中,可能某一個企業研發了一個非標準的特殊性能,往往就拿這個性能去控標,讓很多小企業連參與的資格都沒有。”何振說,建立標準,是為了給國內企業提供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但從長遠來看,存儲領域發生的這場供需失衡的修復期,或許將比預想中更漫長。比如,趙海軍分析認為,存儲行業的新進入者產品驗證周期長達16個月,從研發到量產需要時間,這意味著新增產能無法在短期內填補目前的缺口。楊伊婷亦表示,即便現在存儲原廠決定增加投資,實際的新增產能釋放也要等到2027年或2028年。
這意味著,存儲芯片的缺貨與漲價,可能是一場還要持續兩三年的持久戰。在某種程度上,這似乎也是一種黑色幽默:大洋彼岸的科技巨頭們為了AI豪擲千金,但這筆昂貴的“賬單”,最后可能還得由普通人來支付——明年想換個新手機,恐怕得多掏不少錢。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