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9-24 13:33

![]()

如果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揭示了金融體系的脆弱,那么2020年之后的疫情與量化寬松則讓全球經(jīng)濟體暴露出更加深層的隱患:高企的債務、脆弱的財政、不斷積累的社會不平衡。全球正在進入一個“債務時代”。美國財政赤字刷新歷史紀錄,歐元區(qū)內部財政平衡日益困難,新興市場在美元加息周期下外債承壓,中國則在房地產(chǎn)調整與地方債問題中尋找新平衡。與此同時,地緣沖突愈發(fā)激烈,科技浪潮帶來新的生產(chǎn)力躍升,卻也放大了國家之間的分化,加劇了國家之間的競爭與沖突。
一個國家的債務及其增長是否存在極限?一個負債累累的國家是否會破產(chǎn)?倘若會,那又將引發(fā)怎樣的連鎖反應?橋水基金創(chuàng)始人瑞·達利歐的新作《國家為什么會破產(chǎn)》無疑直擊要害,深刻地回答了這些問題。這本書的主題和思路,延續(xù)了他在前兩本書《債務危機》《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的一貫關切:經(jīng)濟運行背后的周期邏輯,以及國家興衰的深層規(guī)律。達利歐通過對主要國家的歷史長周期回溯和數(shù)百年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分析,總結出國家為什么會在看似繁榮的時刻突然陷入財政破產(chǎn)、貨幣貶值乃至社會動蕩的邏輯鏈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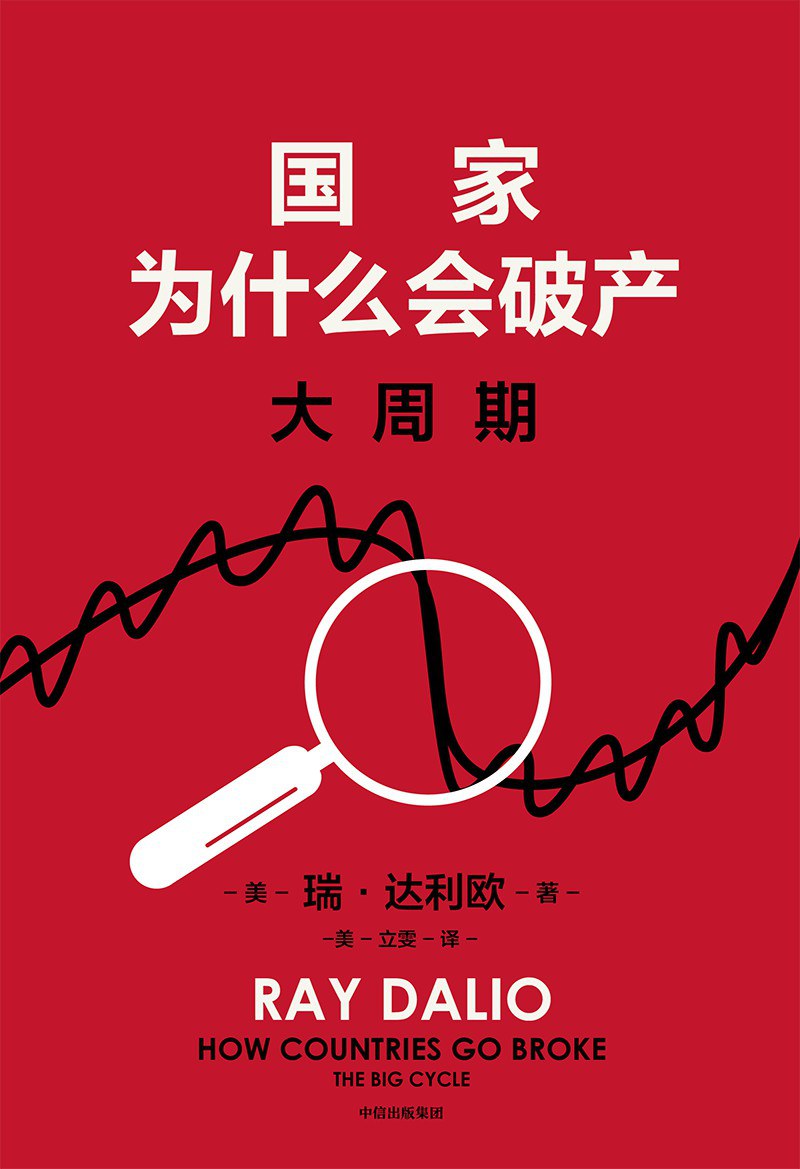
《國家為什么破產(chǎn)》
[美] 瑞·達利歐| 著
[美] 立雯|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6月
這本書值得關注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抽象的學術分析,而是帶有強烈現(xiàn)實指向的“周期寓言”。
大債務周期:理解國家破產(chǎn)的密碼
理解債務周期,就掌握了國家命運的密碼。本書的核心概念無疑是達利歐提出的“大債務周期”。這種周期包括短期債務周期和長期債務周期。短期債務周期通常發(fā)生于利率下行階段,此時央行的貨幣政策會刺激借貸和投資,推動資產(chǎn)價格上漲,經(jīng)濟活動和通貨膨脹指標也隨之上升,直到這些指標超出目標水平。而后,貨幣和信貸供應開始收緊,利率變得相對較高,導致借貸和投資減少,進而造成資產(chǎn)價格下跌、經(jīng)濟活動放緩、通貨膨脹回落,形成一個完整周期。這個周期通常持續(xù)6年左右,上下浮動3年。正是短期債務周期的不斷積累形成了長期債務周期。
短期債務周期和長期債務周期的區(qū)別在于中央銀行是否能通過政策扭轉。具體而言,當債務性資產(chǎn)與負債規(guī)模遠超收入基數(shù)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將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利率水平必須既滿足債權人的收益目標,另一方面又要匹配債務人的承受能力。此時,短期債務周期的經(jīng)濟調節(jié)機制因失效而終結,而長期債務周期則因債務負擔突破可持續(xù)臨界點而崩潰。書中強調,國家破產(chǎn)往往不是突然的,而是長期債務累積與制度性幻覺的結果。所謂“幻覺”,指的是社會在繁榮表象下對債務風險的系統(tǒng)性忽視。
達利歐把大債務周期比喻為一種生物或者疾病的演進過程,每個階段都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癥狀”。通過識別這些“癥狀”,我們就能大致判斷周期所處的階段,并能夠預期未來的發(fā)展。一般而言,大債務周期可以被分為5個階段,不同階段的貨幣政策也會隨之改變。第一階段在周期的起點,國家往往處于低負債、高增長的“黃金狀態(tài)”,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引導信貸流向生產(chǎn)性領域,避免債務空轉。當債務增長會推動生產(chǎn)力提升,從而創(chuàng)造足以償還債務的收入。這將提高人們對財富增值的信心。
第二階段,債務及投資增長超過了當前收入所能支撐的水平。此時經(jīng)濟增長慣性延續(xù),市場樂觀情緒升溫,周期滑入“泡沫擴張階段”,央行的貨幣政策往往陷入“兩難陷阱”——既要維持增長,又不愿刺破泡沫,最終選擇“被動寬松”。
第三階段是泡沫破裂的時期,當經(jīng)濟持續(xù)過熱,通脹壓力突破政策目標,或資產(chǎn)泡沫風險引發(fā)擔憂時,央行不得不啟動加息,但此時債務規(guī)模已達高位,利率上升會瞬間放大償債壓力,形成 “加息-償債能力下降-經(jīng)濟收縮” 的惡性循環(huán)。
隨之而來的便進入了第四階段,艱難的去杠桿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xiàn)為,社會各部門為了還債不得不選擇拋售各種資產(chǎn),如政府國債、股票等,引起資產(chǎn)價格暴跌,居民減少消費、企業(yè)減少投資等。此時央行不得不選擇債務重組或者繼續(xù)增發(fā)貨幣減輕債務壓力。當經(jīng)歷了艱難的去杠桿過程后,經(jīng)濟會逐漸恢復平衡并進入第五階段,新周期也隨之開啟。此時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從應對危機轉向修復增長。
在今天的全球語境下,這一周期模式依舊具有解釋力。美國國債總額已超過GDP的120%,赤字仍在惡化;日本在超高負債與負利率之間艱難維系;許多新興市場在美元周期下外債壓力沉重。這里最值得反思的,是達利歐所指出的“制度性幻覺”:在債務驅動的繁榮中,政策制定者、資本市場與公眾往往形成合謀,選擇性地忽略風險。社會在短期的繁榮中享受“泡沫紅利”,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往往是貨幣信用與國家財政的最終破裂。在長期視角下,這是否正在重演“破產(chǎn)的宿命”?
沖突與秩序:各種周期相互交織
以大債務周期為核心,達利歐在書中又進一步提出“整體周期”框架——他認為,貨幣政策并非獨立變量,而是嵌套在“外部秩序、內部秩序、技術進步、自然災害”四大文明要素中,這些要素通過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效性與傳導效率”,最終決定債務周期的走向。因為脫離文明要素談貨幣政策,就像脫離土壤談種子生長。因為同樣的政策,在不同國家會產(chǎn)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國家的破產(chǎn)也往往出現(xiàn)在“大國周期”中秩序更迭的臨界點,這是外部秩序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比如冷戰(zhàn)時期的蘇聯(lián)就是典型案例:在與美國長期軍備競賽中,蘇聯(lián)將巨額資源投向軍事工業(yè),最終導致財政透支與經(jīng)濟停滯,債務壓力在體制內部失控,國家崩潰。
達利歐提醒,類似的結構性財政壓力,往往是國家陷入債務危機的重要觸發(fā)點。此外,世界秩序的更迭往往也伴隨金融霸權的轉換。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十九世紀的英國、二十世紀的美國無不如此。當霸權國在債務透支、貨幣濫發(fā)與金融體系僵化中失去優(yōu)勢時,新的國家往往會崛起。美元的信用正在經(jīng)受前所未有的考驗。高赤字與政治撕裂讓“美元信用危機”的討論逐漸進入主流。與此同時,數(shù)字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等新議題正在重新定義全球貨幣秩序。達利歐并未斷言霸權更迭的必然性,但他指出:金融霸權從來不是永恒的,它背后依賴的是國家財政的可持續(xù)與制度的穩(wěn)定。
內部秩序則圍繞著一個國家的政府體制和權力斗爭展開。書中談道:“秩序的變化是由那些擁有最大權力的人推動的,他們決定事情的走向。當那些不掌控現(xiàn)有秩序的人獲得了比掌控者更多的權力,并希望改變秩序時,秩序就會發(fā)生變化。”當政治極化時,貨幣政策等可能演化為政治博弈的工具,比如美國兩黨關于債務上限的問題博弈、美聯(lián)儲何時降息的博弈、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不同時期的治理機制博弈等。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發(fā)展時期,金融、政治、軍事、法律等力量此消彼長,共同塑造內部秩序。
技術進步作為“整體周期”的一部分,力量不容忽視。縱觀歷史,科技浪潮確實在多個節(jié)點幫助國家走出債務泥潭。十八世紀的英國通過工業(yè)革命躍遷,二十世紀的美國借助信息技術維持霸權。達利歐認為,今天的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清潔能源等浪潮,或許能為負債累累的國家?guī)硇碌脑鲩L紅利。然而,他也提醒:科技浪潮并不會自動解決債務危機。相反,它可能帶來社會分化與財富再分配的劇烈沖擊。如果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科技紅利可能被少數(shù)資本占有,反而加劇社會矛盾。
盡管書中對自然災害的論述篇幅有限,但達利歐仍將其列為整體周期的關鍵變量——自然災害通過摧毀經(jīng)濟資產(chǎn)、增加應急支出,倒逼貨幣政策“被動寬松”,最終形成“災害-債務-通脹”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與其他力量一樣,自然災害也與其他重大力量交織在一起,塑造著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例如,發(fā)達國家面臨的移民問題(氣候變化導致的移民壓力)和欠發(fā)達國家面臨的生存環(huán)境問題(人們正努力適應干旱、洪水和其他變化)顯然因自然災害的增加而惡化”。
以史為鑒:典型國家的發(fā)展經(jīng)驗
書中最引人深思的部分,是達利歐對美國、中國、日本三大經(jīng)濟體的周期性剖析。這不僅是對三國命運的分析,更是對世界經(jīng)濟未來發(fā)展的注腳。
首先是美國,書中回顧了美國自1865年到2025年近200年的發(fā)展,揭示了不同周期如何交織。達利歐判斷,美國自1945年—2024年共經(jīng)歷了12個完整的短期債務周期,現(xiàn)在正處于第13個周期的約2/3處。這些周期平均長度約為6年,累積形成了一個大債務周期,導致中央政府債務收入比上升,使中央銀行的資產(chǎn)負債表惡化。
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債務周期始終與美元霸權深度綁定,形成了“以儲備貨幣地位支撐高負債,以高負債維持霸權地位”的獨特模式。美國是當今最典型的“高債務+高消費”經(jīng)濟體。其強大之處在于美元霸權與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力,這讓美國能夠在赤字惡化的情況下繼續(xù)融資。達利歐提醒,美國當前的挑戰(zhàn)在于財政赤字不可持續(xù),國會的政治僵局使得債務調整困難;美元信用在多極化趨勢下面臨侵蝕;社會分裂削弱了制度的統(tǒng)一性。然而,美國的優(yōu)勢在于強大的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在AI、清潔能源、生物技術等領域,美國依舊擁有領先優(yōu)勢。這意味著,美國可能通過科技浪潮延緩甚至突破債務周期的宿命。
其次是日本。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后,努力學習西方的各種制度,而后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自1945年—1990年,日本重建并發(fā)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強國。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積累了巨額債務成為資金泡沫,這個泡沫在1989年—1990年破裂,此后一直對日本造成嚴重的削弱效應。
達利歐認為日本在1990年—2013年采取的去杠桿模式并非最佳,他在書中說道:“盡管日本有能力實施一場‘和諧的去杠桿化’,因為其幾乎所有債務都以本幣計價,幾乎所有棘手的債務人與債權人關系都發(fā)生在國內,且日本對世界其他國家還是凈債權人,但它的做法與我描述的‘和諧的去杠桿化’應采取的步驟完全相反。”
對于這輪債務周期,日本政府開始并沒有積極地進行債務重組和債務貨幣化,以至于泡沫破裂后對央行和居民的資產(chǎn)產(chǎn)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經(jīng)濟長期低迷,通縮壓力難解;人口老齡化加速,財政支出剛性上升;政策空間極度受限,對外部沖擊缺乏彈性。這一情況直到安倍政府上臺后方才有所好轉。達利歐認為,日本提供了一個“低增長、低通脹”的生存樣本,但這種模式并不可復制。對美國或中國而言,日本更像是一個警示:高債務可能會對應一個長期的“潛在停滯”陷阱。
最后是中國。達利歐認為,中國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歷了“債務積累-債務解除-債務積累”的重復過程,導致財富無法積累,也很難產(chǎn)生良好的信貸和資本市場。這一情況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好轉,標志是開始構建自主的資本市場。直到今天,社會經(jīng)濟制度已經(jīng)從一個典型的低效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發(fā)展到一個高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
他在書中談道:“我目睹了中國的整個轉變過程:中國從努力應對貧困和地緣政治劣勢,到通過市場改革開放政策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財富增長和地緣政治力量,再到如今必須應對這些更大的財富和地緣政治力量帶來的挑戰(zhàn),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貧富差距、機會不平等,以及重大的國內和國際沖突。”
達利歐對中國的分析頗具耐心。他認為中國正處于從“債務驅動增長”向“高質量發(fā)展”轉型的關鍵階段。面臨著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高企,房地產(chǎn)泡沫尚未完全出清;人口老齡化加速,對財政形成長期拖累;全球地緣競爭環(huán)境趨緊,外部增長空間受限等問題。但中國的優(yōu)勢在于制度韌性和社會動員能力。與許多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在危機中往往能集中資源進行結構性調整,這讓它在周期反轉時具有更強的緩沖力。達利歐判斷,債務問題將會是中國發(fā)展中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政府有能力實現(xiàn)“和諧的去杠桿”過程,但是能否避免“日本式停滯”,取決于債務處理方式、科技突破與社會治理的平衡。
美國的霸權挑戰(zhàn)、中國的轉型考驗、日本的債務泡沫,都在提醒我們:繁榮與破產(chǎn)之間,并沒有永恒的安全區(qū)。唯一的出路,在于對周期的認知,以及在科技與制度創(chuàng)新中尋找新的錨。
《國家為什么破產(chǎn)》展現(xiàn)了一種“周期的視角”。它告訴我們:國家破產(chǎn)并非偶然也非宿命,而是取決于如何平衡好債務、內外部秩序、技術進步和自然災害等因素。對于個人而言,這本書教會我們識別所在國家的債務周期階段,判斷內部秩序、外部環(huán)境等要素對貨幣政策的約束,從而理解債務政策的底層邏輯,規(guī)避 “周期誤判”的風險,做出明智的決策。正如書中所言:“債務危機既蘊藏重大風險,也孕育巨大機遇。歷史證明,它們既能摧毀帝國霸業(yè),也能為深諳其運作規(guī)律且掌握應對原則的投資者創(chuàng)造絕佳投資機會。”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